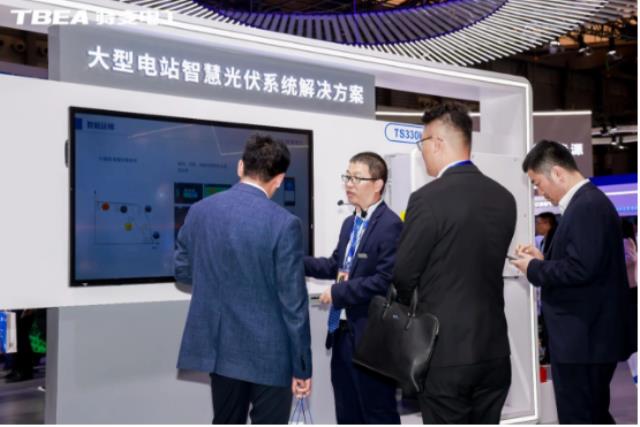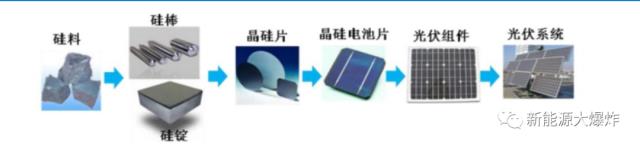其實國有資本從來就沒有缺席過中國光伏產業,只是這次不同了。在科研和加工環節,1997年之前,是國有資本撐起了中國光伏。2001年的時候,是國有資本幫助無錫尚德開始了中國光伏引領世界的時代;在應用環節,2011年,國有資本曾經占據國內光伏電站的半壁江山。只是那時,光伏對國有資本是商業機會,是國家任務,而2018年開始,光伏對國有資本是戰略機會,是戰略進入。
有文章從國家能源集團當前投入光伏產業的金額發問是否“戰略”?其實一個戰略的早期執行,常常是和認知有關,和投入金額不一定有關。一個需要金額才能證明是否“戰略”的分析,應該是個落后別人半條街的分析。
作為全球最大煤炭生產、最大火力發電、最大風力發電和最大的煤制油煤化工公司的總經理,凌文說:“早在8年前,神華低碳研究院一支科學家團隊,就開始跟蹤銅銦鎵硒薄膜光伏電池技術……國家能源集團將成為全世界銅銦鎵硒薄膜光伏發電技術的領導者之一”,其光伏“戰略”意圖明顯。而老紅參與意見的大型國有能源企業光伏產業投資報告中,字里行間也是“戰略”意圖明顯。
從中國經濟改革考慮,老紅曾經強烈反對國有資本進入光伏產業。2012年底,剛進入光伏產業的老紅就向資深能源專家表達過這一看法,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對此無可奈何的笑而不答。
過去十年,中國新能源產業云蒸霞蔚、江河橫流,光伏產業已經成為唯一由民營資本打造的中國名片,曾經領先的風電,因為國有資本尚未退出主角只能扮演追趕的角色。2008年至2017年的10年間,中國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年均增長分別為44%和191%。而2006年至今,可再生能源能源補貼資金總計支出超過了3200億元,其中風電享受補貼超過了一大半。
伴隨光伏產業已經來到重大突破的時刻,反對國有資本進入的看法也到了必須修正的時候。
國有資本戰略進入光伏,既是不可阻擋的事實,更是光伏產業長期穩定發展的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光伏產業的突破時刻,需要國有資本的助推。當前,光伏人都會有一個共識:盡管還有諸多不確定,但是只要有足夠的資本力量,就可以把光伏產業推上最具競爭力能源的臺階。就像要把水燒開,還差最后一把最干的柴火。只是這一資本力量,民營資本是不夠的,國有資本不可或缺。比如“國家能源集團總資產超過1.8萬億,今年上半年凈利潤402億元……比光伏全行業2016年總產值3360億元還要高出約50%......是2017年盈利能力最強的20家光伏上市公司凈利總額約155億元的2倍還多。”
第二,光伏資產的中期持有需要實力雄厚的國有資本。未來光伏資產的投入和持有是一個天文數字,需要各種實力雄厚的資本。理論上,中國光伏資產持有的遞延規律也應當是:民營資本建設,國有資本中期持有,風險資本長期持有。有統計說,當前中國光伏電站資產已經達到萬億規模,到了需要國有資本中期持有的時候。不久前,先是愛康科技將裝機容量503.53MW的光伏發電資產包轉讓給浙能集團,“帶來包括交易對價(轉讓價9.66億元)、往來款以及剝離的補貼收入等合計約24億元現金流,減少有息負債23.09億元。”;后是協鑫新能源以3.06億出售180MW光伏電站80%的控股權給中廣核太陽能。
第三,傳統能源資本轉戰新能源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從認知角度講,無論是新能源資本還是傳統能源資本,新能源必將替代傳統能源已經成為共識;從資本趨利角度講,新能源的投資機會正在越來越大,任何資本的趨利趨勢是不可阻擋的。2012年一家大型國際能源企業宣布退出光伏產業,2016年又宣布重回光伏產業就是最好的證明。在中國,傳統能源資本必然轉戰新能源,而國有資本幾乎是傳統能源資本的唯一代表。
不管民營資本為主的中國光伏產業是歡迎還是不歡迎,國有資本都來了,而且是戰略的來了。對此,民營光伏資本不是選擇高興不高興的問題,而是選擇怎么合作的問題。